【現代人文文庫】
由韓愈「文以載道」看儒家思想與文學藝術的問題
方世豪(香港人文學會會長、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內容介紹
文學藝術作品和人格修養的關係,歷來有不同派別理論家的爭論。而中國文化中,儒家思想對人格修養有深遠影響,本文會根據徐復觀先生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中《儒道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一文的內容,說儒家人格修養和文學藝術的關係,其中主要根據韓愈《答李翊書》內容作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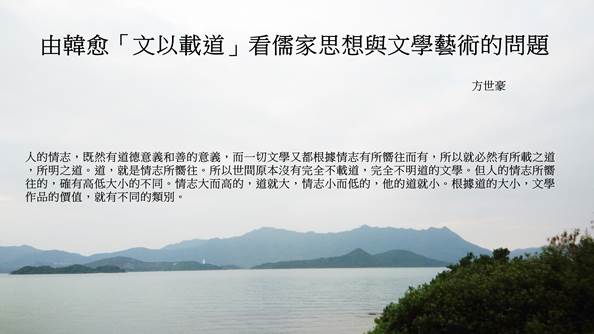
內文摘錄:關於文以載道
我們的說法,是以文學本源於人的情志要求而說。這個情志要求,有道德上善的意義,和文學中的故事和境界要有結構和真理。這說法和一般的說法頗有不同。
在一般的說法中,或者有人以為文學只敘述客觀事物就可以,可以不涉及主觀的情志,好像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文學觀。
又或者以為文學可以只寫一個心靈的直覺靜觀境界,和情志無關,好像直覺主義的文學觀。
又或者有人以為,如果文學一定要表現情志,這個情志又一定包涵善的意義,就會妨礙純粹的美,而不能說明何以罪惡的事物也可以是美,好像波特萊爾所講「惡之花」,這是唯美主義的文學觀。
波特萊爾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象徵派詩歌之先驅,現代派之奠基者,散文詩的鼻祖。代表作有詩集《惡之花》。《惡之花》出版後不久,因為「有傷風化」的罪名,法庭處以波特萊爾三百法郎的罰款,並勒令從詩集中刪除六首主要的詩,當時的法國文壇對此事件的看法一分為二,只有少部分人站在波特萊爾一邊。波特萊爾認為,美不應該受到束縛,善並不等於美,美同樣存在於惡與醜之中,是唯美主義文學觀。
又或者有人說,如果著重文學的道德意義,或善的意義,文學應該都是志在明道或者載道,好像傳統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這說法中,很多文學的內容,都應該大為減少,而純粹的自然山水文學,就不足以說是文學。
又或者有人以為,只要有文學上的技巧,一切事物都可以進入文學。這說法是,如果根據我們的意思,說文學要表現情志,人的情志對事物或境物,一定有所選擇。有這個選擇,就好像一定要設定若干事物或境物。這些事物,就好像在未經過文學技巧加以表現以前,已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這是很難明白的。所以不如說一切事物或境物,原本沒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而任何事物或境物,只要經過文學技巧加以描寫,就都可以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這可以稱為技巧主義的說法。
以上這些說法都不是我們所取的,現在可以一一加以解釋、去除疑滯,而論證我們以前所講的說法。
照我們的意思, 世間決沒有純粹敘述客觀的事物的文學。因為文學的敘述,必定有所選擇,而不是一切客觀的事物,都可以進入文學。這個意思,原本容易明白。如果明白這個意思,一個文學家選擇這個事物,而不選擇其他事物,就只能夠由文學家自己的情志,加以決定。這個決定後的寫作,就表現這個決定是怎樣的,也表現他的情志是怎樣的。所以說,文學不表現情志的說法,實在是錯的。
有人說,文學只需要形成直覺的境界,而應忽視文學中情志的存在。這說法的根本理由,常常在對於情志的認知,只知道有積極的情志,而不知道有消極的情志。積極的情志,即是一般有確定的方向,還有目的,而求實現在外在世界的情志。而消極的情志,則常常是由一般積極的情志中,超拔出來的一種情志。棲棲遑遑,是一種積極的情志。歸去來兮,是一種消極的情志。向著一個境界有歡欣興趣,是一種積極的情志。超拔舊境,淡然若忘,是一種消極的情志。
凡是人有興趣的境界,多少都會超拔一個境界,亦即需要超拔於我們原來的一個情志。唯有由這個超拔,才有境界的開拓、生長和發展。人亦可以超拔於一境界和原來相對的情志,而不必趨向新境界。亦即由此超拔一境界的活動本身,和原來對之有情志的這個境界,互相結合而形成一個新的境界。這就是由忘記境界、無境界,而形成的境界。王維詩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即是有人聲而忘記人的形,無人形的境界。
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空寂的山中不見一個人,只聽到一陣人語聲。太陽的餘暉返入深林,又照到林中的青苔上。)
唐天寶年間,王維在終南山下購置輞川別業。鹿柴是王維在輞川別業的勝景之一。輞川有勝景二十處,王維和他的好友裴迪逐處作詩,編為《輞川集》,這首詩是其中的第五首。
第一句「空山不見人」,寫空山的杳無人跡。王維特別喜歡用「空山」。「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山居秋暝》,「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鳥鳴澗》。「空山不見人」,表現山的空寂清泠。但在「空山不見人」之後緊接「但聞人語響」,卻境界頓出。在一切杳無聲息之中,偶爾傳來一陣人語聲,卻看不到人影。這「人語響」,是空谷傳音,愈見空谷之空。空山人語,愈見空山之寂。這境界亦是一「忘卻對有形的人的一切情志」的境界。
由此我們就可以說,這樣的文學只呈現一個境界,或表現一種胸襟、一種神韻,而好像和人的情志無關。其實這個境界的呈現,正由於人對原來一般人間世俗的情志,而另外生出一超拔情志,然後才有這個超拔的情志。雖然是消極的情志,但仍然是情志,不能說不是情志。
有人說,著重情志和道德意義、善的意義,就一定會妨礙文學的純美。其實也不一定的,因為文學一定要依靠情志而有故事和境界,所以文學所敘述的故事和境界的美,一定不能離開人的情志。人的情志,原本不能沒有一道德意義和善的意義。
而世間上提倡唯美主義者,是否能夠完全沒有他自己的道德標準,用來分別善與不善的標準?這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好像以驚世駭俗作為題材,就是要描述驚世駭俗,以反世俗作為善,作為道德。例如:尼采反對世俗的奴隸道德,就主張一種超人的道德。又例如:十九世紀唯美主義劇作家,王爾德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其實亦不是說藝術完全不表現人生,他其實只是想提倡表現人生另一面的藝術。所謂人生的另一面,就是他認為值得表現的,無意間就是以這一面作為善。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說,罪惡亦有花。當然,例如:妓女和盜匪也有光輝。但這光輝本身,仍然代表一種生命的價值和人格價值,不能說完全沒有善的意義或道德的意義。罪惡有花,是由於罪惡同時包含特定類別的善的意義或道德的意義,並不是純粹由他的罪惡而發展出來。
至於人描寫罪惡,寫到窮形極惡,仍然可以是一種美的文學,這種美就是文學技巧的美。這種美,就是因為能夠通觀罪惡,欣賞罪惡的因果,其中有同而不同,表現出罪惡世界的內在結構。這種通觀本身,就依靠文學家心靈的通達,能夠不偏不蔽於罪惡的某一面,而常常能夠運行自如,運行於罪惡之上的各方面,這樣才能描寫罪惡的情志。這心靈情志,不能說只是罪惡,而完全沒有善的意義或道德意義。
由此而說,說文學依靠情志,情志有善的意義、道德意義的說法,其實並不妨礙文學作品自身具有純粹的美。而且也正可以說明這種純粹的美的表現如何可能。
我們這種說法,和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的關係,就是:人的情志,既然有道德意義和善的意義,而一切文學又都根據情志有所嚮往而有,所以就必然有所載之道,所明之道。道,就是情志所嚮往。所以世間原本沒有完全不載道,完全不明道的文學。但人的情志所嚮往的,確有高低大小的不同。情志大而高的,道就大,情志小而低的,他的道就小。根據道的大小,文學作品的價值,就有不同的類別。
人應該嚮往於道的大而高的。傳統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即是說文人寫的文學,應嚮往於道的高而大的。這個意思無可逃避,亦即是由文學的原本無不載道、無不明道而確立。如果小道可貴,大道自然應該更加可貴,因為大是小的累積而成。如果卑道可貴,高道就更加可貴,因為高是由卑累積而成。人豈可以自安於卑小之道,而不求高大的道呢?有嚮往高大之道的情志而有的文學,又有嚮往卑下之道的情志而有的文學,但人又豈可把兩種文學相同看待呢?
至於有文學家嚮往高大的道,是否就歸於只著重直接講道的文學?這就不完全是了。因為人固然可以將他的情志所嚮往的道,由文學間接表現,而人的消極情志表現,也可歸於只要求一境界而呈現。由產生出文學的情志,和情志所嚮往的道的大小高低,是文學價值有關的一方面。
閱讀全文,請訂閱人文學會Patreon。連結為:
前往現代人文文庫:
http://www.hksh.site/modernhumanities.html
※請前往人文臉書讚好、分享或評論:
https://www.facebook.com/modernhuma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