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語言與開顯:實體的概念是怎麼來的?
主講者:唐力權(前美國康州美田大學教授、已故國際著名哲學家)
摘要:
本文是前美國康州美田大學教授、已故國際著名哲學家唐力權教授,於2009年在四川大學舉行哲學講座的講辭記錄。
本文的目的乃是通過作者的場有開顯論的觀點來剖釋或探討一組相互關涉的哲學問題。場有哲學的一大特色在於它底非實體主義〔或簡稱非實體〕的立場。作者認為,實體與非實體之爭衡過去已有過不少討論,但也引起了不少誤解。但隨著場有哲學一些概念和表達方式或語言的轉變,這個論題有重新處理的必要。實體的概念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在人類在人文化──文明化的過程中對開顯者的開顯所表現的姿態上。
關鍵詞:
唐力權 場有哲學 場有開顯論 非實體主義 實體 形上學 本體論 存有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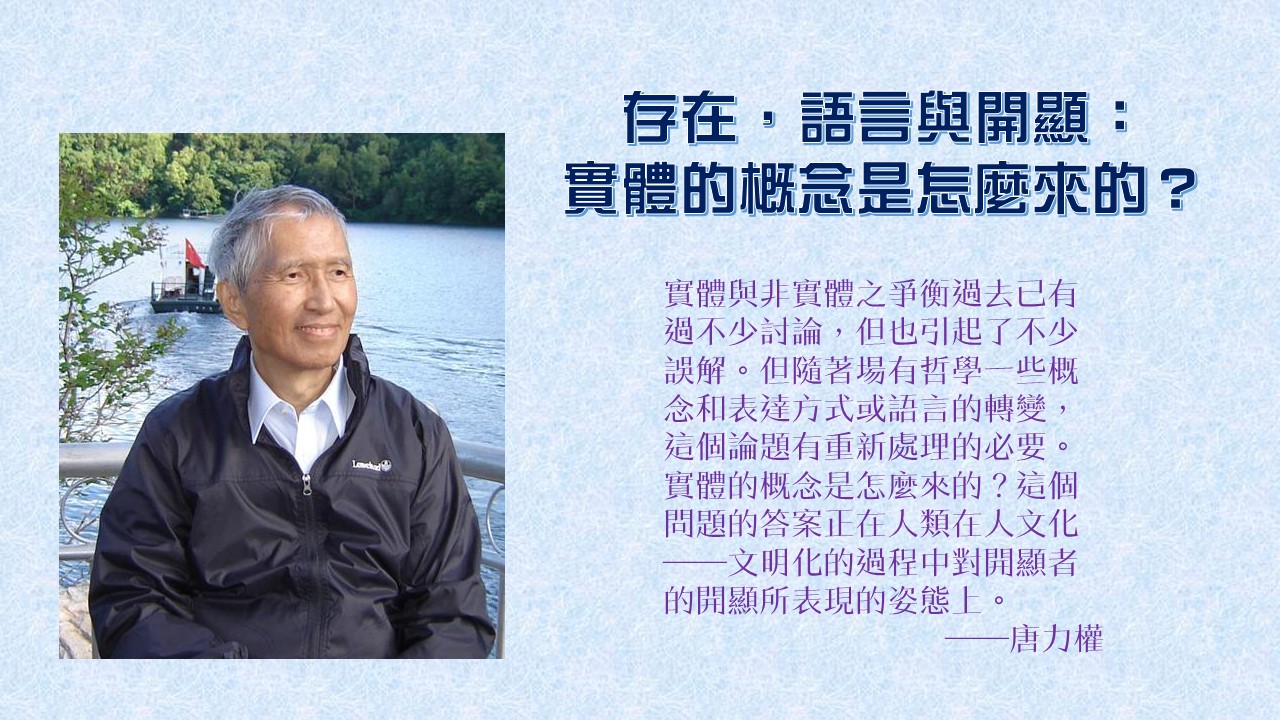
何謂存在、有、或存有?這是西方古典哲學家鄭重提出的一個核心的哲學問題。阿里斯多德所謂的「第一科學」〔prote philosophia / first philosophy〕, 即後世所稱的形上學〔metaphysics〕,本體論或存有論〔ontology〕,正是以存在本身to on he on / being ua being為研究或思考對象的一種學問。希臘文on或ontos乃是連綴動詞「是」〔eimi / be〕的動名詞,用來表達一事件或活動作用正在進行中的存在狀態。大概創造古代希臘語的泰古人認為進行式的語法最能表達他們的存在體驗,所以他們就以「是」的現在分詞on或ontos來指稱存在或存有。如是,存在論在西方也就成為「是論」,以「是」的意義和語法來把握存在體驗的理論。這門最具西方哲學特色的學科在東方的哲學傳統裡是找不到的,印度沒有,中國更沒有。漢語並沒有與希臘和其他印歐語系的「是」相當的語法。但這表示什麼呢?東方哲人沒有把存在本身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來探討,是否就表示東方哲人就沒有存在的關注和思維或甚至沒有存在的體驗呢?當然不是的。事實上,存在的體驗是人所共有的,存在的思維則更是哲學思維的本質所在。不管在那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存在的關注和存在的意識和思考都是文明人之所以為文明人最突出的標誌。為什麼這樣講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文明的本質,文明之所以為文明,其關鍵正在文明人類對存在的特殊的體驗和把握上。漢語裡沒有存在意義的「是」,所以中國哲學沒有「是論」。古代中國哲人是通過「道」的語言和漢語的語法來表達和把握他們底存在體驗的;「道論」才是中國哲學的存而理論。
阿里斯多德把「是論」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探討牽涉到一個大前題,即: 存在本身是可以與存在者〔onta / beings〕分開來把握的。在阿氏的哲學體系中,這就是「是論」與其他學科如物理學、生物學或我們所謂的「所是學」〔或「所是論」〕的分別。「所是」指的是存在者,「所是學」就是研究不同種類或類型的存在者的學問。但這個「是」與「所是」──存在本身與存在者──的二分法是不會被東方的哲人所接受的,在印度不會,在中國更不會。在東方的文化和哲學傳統裡,存在本身是不能與存在者分開來把握的,因為存在的體驗與存在者的體驗是分不開的,是超切不離的。沒有離開存在者的存在,「是」乃是〔所是〕中的「是」;存在本身的體驗就在存在者的體驗之中。在中國哲學或「道學」的傳統裡,是與所是的分別就是道與萬物的分別。道在萬物,沒有離道之物,也沒有離物之道,因為道正是萬物之道。對中國哲人來說,道的體驗與物的體驗是無法分割的,把它們分割了也就無道無物了。西方哲學的是論是一個「超離主義」的存在論,而中國哲學的道論卻是一個「超切主義」的存在論,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尤有進者,西方哲人的超離二分法不僅表現於存在與存在者或是與所是的對比上,也應用在「第一所是」或「第一存在者」與「後繼所是」或「後繼存在者」的關係上。不管是阿里斯多德的「第一動因」(First Mover) 或是中古神學的上帝、造物者、或「至高存在」(Supreme Being) ,第一所是與後繼所是的關係本質上是外在的。上帝或造物者原則上可以創造萬物,也可以不創造萬物。前者與後者並無必然的內在關聯。但在中國道論的「溢出」宇宙觀裡,作為萬物之母或第一所是,道是萬物的本根,萬物生於道的動態本質;宇宙間的任何一物都是道的化身,來自本根權能一體之分殊。這就是《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段「道生一,二生三,三生萬物」所涵攝的精微義蘊。由於萬物生於道的動態本質,萬物與道與的關係就好比我們與我們底祖先的關係一樣,是超切地相依而不是限隔地超離。
「道」字有說話的意思,言說義的「道」與希臘語「羅高斯」或「羅高」(logos) 相當,其在中西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也相似。但言說 (speech) 和語言(language)不同,言說是激活語言中的存在體驗的生命活動。海德格的名言「語言是存在的「安宅」“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並不準確或只說對了一半。用西方哲學的實體語言來講,「安宅」就是「載體」〔substratum / hypokeimenon〕的意思。嚴格地說,語言不是存在的載體 ,而是存在體驗的載體。但在海德格和其他現象學者的心中,住在語言「安宅」中的不是存在體驗的原始資料而是為文明人類意識指向性對象的「意義」──概念性的意義。存在體驗中的那些非概念性的成份或未經概念化的意義,現象學者是不在乎的,抑且是不會接受的。原始的存在體驗直接來自實存生命的活動作用,故作為存在體驗的載體,語言與實有(包括所有自然界和人造的具體物) 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道又有道路的意思,這個含義的重點與其說是在道路本身不如說是走在路中的人和相對於走路的人所開顯的境界。言說與語言的關係就好比走在路上的人與相對於他而呈現的境界的關係。言說激活了潛存在語言中存在體驗,一個新的存在境界也就通過被激活了的體驗而開顯了。這就是本於道論的言說觀、語言觀。其超切的色彩當或多或少與漢文字象形表意的特性有關。另一方面,由於印歐語言拼音文字本然的抽象性,西方的語言觀自始即有語音與文字,言說與語言和語義與實有相互脫節的傾向。近現代西方哲學所謂的「語言轉向」究其實正是此超離主義語言觀與心態的終極表現。不管是屬於歐陸陣營的哲學家還是屬於英語世界的哲學家,近世西方哲學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多談語言與言說而少談或根本不談實有或實在。宇宙與萬物的實相和本質終究是難以或不可能以實體性的概念思維來把握的。後現代的西方哲學家整體上可說是已徹底地放棄了這種企圖。他們大概認為唯一能被知解理性把握的就是言說與語言。他們把語言孤立起來,視為一個可與宇宙的具體真實分離的實體或領域;他們把言說孤立起來,把它與我們的身心及其他實存生命的實踐或活動作用分隔。不過,離開宇宙和萬物的具體真實我們還能把握語言麼?離開了我們的身心和實存生命的行為和實踐,我們還能把握言說麼?到頭來,語言與言說的本質終究也是不能被把握的了。
籠統的講,我們所謂的「實體」乃是一個獨立自存、同一不變、完全可以被概念思維或知解理性或我們所謂的「羅高理性」把握的東西。「獨立自存、同一不變」這八個字是關鍵。因為實體之所以能完全為知解理性所把握正由於它的固定性、確定性與不可分性。而這正是巴門尼德斯為存在設準的「一」──「絕對的一」。西方古典哲學家如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的「實有」或「實在」〔the really real / to on he on〕觀念就是以這「絕對一」為存在標準而立義的。「絕對一」是無對的,它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它的對立面就是「無」──「絕對的無」。絕對的無就是絕對的不存在,因為它是完全不能被羅高理性所把握的。以上就是實體一概念的邏輯根源。「邏輯」乃是為概念思維設準或立極的學問,它的最高原則就是巴門尼德斯的絕對一。為阿里斯多德所創立的古典邏輯或形式邏輯正是以此原則為大前題而建立的。形式邏輯所謂的「思想三律」──同一律、矛盾律與排中律──不過是「獨立自存、同一不變」這八個字的演繹與形式化吧了。所以形式邏輯與本體論在本質上是同源的,它們是絕對一這個大前題的孖生兄弟。「本體」就是實有或實在,真實的有或存在。存在本身與存在者──是與所是──分離之後,西方哲學家自古典時代開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實有或實在的探討上。他們討論的焦點不是being as being / to on he on 〔存在本身〕而是 to ontos on / the really real 〔真實的存在〕 。柏拉圖與阿里斯多德的結論是:實有或實在必須是一個「實體」〔substance / ousia〕,一個滿足知解理性底邏輯標準的真實存在:若不是絕對是自身就是絕對是的「副本」或「抄本」。換句話說,獨立自存、同一不變乃是實體之所以為實體的特性,或我們所謂的「靜態本質」。故「實體」一詞中的「實」字有兩層意義,一是「真實」的「實」〔real〕,另一則是指涉靜態本質的「實」,代表實有或實在底邏輯標準之「實」,以「固定性與確定性」〔definitness〕為義之「實」。當代中國哲學的實體一詞乃是從英文substance (源自拉丁文substantia) 翻譯過來的。Substance 或substantia 乃是「站在下面」亦即是「托體」的意思。這和它的希臘原文ousia差距很大,完全沒有後者的豐富義蘊,當然就更沒有中文實體一詞的巧妙和貼切了。不過,英文substance 也不是一無是處的譯語。在阿里斯多德的實體ousia理論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是用來處理主-謂式中主詞與謂詞或實體與屬性的關係的。這就是阿氏生成論所依賴的「載體」hypokeimenon (拉丁文substratum) 概念。作為主詞的實體是不能作謂詞用的,因為它是一具體物底屬性的載體,它底生長變化的所在地。這就有點場有哲所謂「場」的意味了。但場有的「場」是開放的,阿氏的載體或場卻是孤立的、封閉的。阿里斯多德的實體論一方面堅持實體的固定性與確定性或獨立自存、同一不變的靜態本質,另一方面則又肯定實體生長變化的動態真實。阿氏哲學的特色就孕育在這矛盾的張力上。
作為哲學的述語, 希臘文on與 ousia 的分別乃是存在與實有或實在的分別。柏拉圖與阿里斯多德雖仍然關注存在本身的問題,但事實上理論焦點已經轉移到存在者和存在者底真實性的問題上,亦即是從「是」到「所是」和「真是」或「真實的所是」的轉移。那些存在者才是真實的存在,真實的所是呢?對這個問題,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給出不同的答案。柏氏以世間萬物的〔靜態〕本質〔eidos〕為真,而阿氏則以具體存在的個體物〔如一個人或一匹馬〕為真。不過儘管見解不同,他們在泛指真實存在者或所是時所慣用的詞就是「奧西亞」(ousia)。 這個字有十分豐富的意涵,翻成英文就是being, essence, substance──存在,本質、實體。熟識西方哲學史的人都知道,這三個概念對西方哲學,尤其是形上學的形成和發展是如何的關鍵和重要。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西方哲學的特色就是通過這三個基本概念表現出來的。
奧西亞ousia乃是連綴動詞「是」〔eimi / be〕的過去分詞〔past participle〕。過去分詞是用來表達曾經是或發生過的事物的。直接的翻譯就是「曾經是的什麼」〔the what was being〕。曾經是或過去了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它已經成為事實;因此曾經是的存在有頑強的固定性與確定性。這就給我們對實體一概念的來源提供一個重要的線索了。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之所以選擇奧西亞或ousia〔曾經是〕而非動名詞on/being〔當下是〕來表達他們的實有或真實存在的概念正本於前者所涵攝的固定性與確定性上。對柏拉圖來說,只有永恆不變的本質才是ousia 或實體,真實的存在者。阿里斯多德則有「第一實體」與「第二實體」之分。前者指的是個別具體物中扮演屬性載體角色的hypokeimenon, 而後者則指的是內在於個別具體物而為其形式因的「類性本質」。雖然與柏拉圖的永恆本質有別,阿氏的屬性載體〔第一實體〕和類性本質〔第二實體〕與柏氏的永恆本質有一個共通性──即我們所謂的「頑強的固定性與確定性〕。而這為真實存在設準的「實體性」正是我們要爭論的問題所在。
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必須是固定或可被確定的東西才是真實的?這是一種假設嗎?還是一種先驗的真理?這個假設或前置的判斷有客觀的根據嗎?沒有。在我們的存在體驗中既有相對地固定或可被確定的一面,但也有相對地不固定或不可被確定的一面。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原始的存在體驗是沒有沒有評論、沒有標簽的,它只是一個自是其是,自然其然吧了。「真實」與「不真實」存在的分別乃是人類──尤其是哲學家或思想家──為滿足其知解理性的要求而投射於萬物的構想。文明人為求生存、求發展就得有效地把握存在,而知解理性通過邏輯思維對存在者的實體化正是文明人類得以在某一意義上有效地把握或控制萬物的一種手段,一種為生命服務的理性道術。這裡「理性」一詞是有兩層意義的。它指的不僅是以邏輯思維、實體思維為手段或工具的知解理性,也兼指以實存生命本身為服務對象的「實存理性」或「生命理性」。後者是高於前者的;不管是如何有效或有力,知解理性只是實存理性的一種功能,而非實存理性本身。說到最後,我們的一切生命活動莫非實存理性的產物。而從實存理性的觀點來看,知解理性對存在的實體化是很有問題的,對文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是可以導至嚴重的後果的。此乃因徹底實體化的宇宙乃是一個四分五裂、斷而又斷的宇宙。莊子所謂的「道術為天下裂」就是針對實體化文明而作的批判。從場有哲學的觀點來說,存在本身是「絕對無斷」的,存在者的世界是「斷而不斷的」,斷而又斷的宇宙──實體化的宇宙──正是一個「有欠真實」的宇宙。「有欠真實」因為它的開顯乃是奠基在存在者場有體性的篾視和存在本身的遺忘。如是,實體主義與非實體主義之爭也就不是我們可以輕易地束之高閣的哲學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沒有其他哲學問題可與倫比的。
「存在的把握」是什麼意思?人是如何把握存在的呢?既然存在的體驗是人所共用的,那麼這是怎樣的一種體驗呢?讓我們對這這個核心的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我們給予的初步答案是:「存在」就是開顯者的開顯。這個定義也許是「存在」一概念再簡單、最直捷、也是最基本的闡述了。但這可不是我們的發明,這句話所指涉、所闡述的毌寧是人類對存在最原初的體驗。沒有不開顯的存在,完全或絕對的不開顯就是絕對的不存在。存在者就是開顯者,而開顯者在某一意義上也必然是一個「在場者」,因為開顯者若完全不在場的,我們就無法體驗得到他的存在或開顯者。「在場的開顯者」──這當是「物」或「事物」,作為存在者的代名詞最基本的哲學含義。如是,存在的定義就應改寫為在場開顯者的開顯。
很明顯的,在這個定義裡已隱含了存在的相對性、多元性、殊性與脈胳性──或統稱之為「場性」。一切開顯都是相對於某一或某一類生命體的開顯。事實上,開顯與生命體這兩個概念可以說是相互定義的,因為廣義的「生命」正是被定義為可以感受和把握開顯的權能。一切開顯都是通過活動作用的開顯,而活動作用正是權能運作的具體存在。故在這個意義上,具體物、權能體和生命體乃是同義語。開顯的相對性,最後分析起來,乃是植根於權能體可分而不可分的超切性。有相對於我的開顯,也有相對於你的開顯;有相對於人的開顯,也有相對於人類之外其他生命體的開顯。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都莫不有其各自開顯的世界,享用著某一型態的具體存在。由於生命體感受功能或能力和傳輸媒介的不同,開顯的形式是多元的、多維度的。就人而言,有通過視覺的開顯,也有通過觸覺、聽覺、嗅覺、味覺等感覺器官的開顯;有通過意識層次的開顯,也有通過無意識、潛意識或甚至超意識層次的開顯;有通過直覺的開顯,也有通過理智或知解理性的開顯;有通過記憶的開顯,也有通過想像的開顯。總而言之,存在的開顯與生命體的感受功能是分不開的。一生命體對存在者或開顯者的把握乃是其感受功能或能力的綜合。這個綜合能我們稱之為權能體或生命體的「拓撲統覺」(topological apperception)。「拓撲」(譯自希臘文topos) 是地方或所在地的意思,這裡用來指稱一生命體或具體物在權能的功能時空中所處的位置。開顯的殊性與脈絡性就建立在權能運作和生命活動的拓撲性上。一切開顯都是特殊的,為權能的拓撲脈絡所決定的。從場有哲學的觀點來講,宇宙乃是一個本於創化權能的超切連續體〔我們所謂的場有〕,萬物中的任何一物都是創化權能〔或簡稱權能〕一體之分殊或化身,連續體中的一個不可被替代的環節。開顯的超切性或場性正來自此權能真實或實在的體一分殊上。
開顯當然不是什麼靜態的實體,而是一個依場而有的創化事件,代表權能「體一」與「分殊」的超切綜合。創化權能是生發的權能,也是開顯的權能。生發與開顯乃是一事之兩面。創化事件依場而生而起,也依場而隱而沒,就好像大海中的浪波一樣,無可避免地受到其場性和拓撲性的限制與支配。作為在場的權能體,人和其他生命體或具體存在是如何在其生發的過程中把握開顯的呢?此句中的「把握」兩字是什麼意思?生命體所把握到的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信息──關於存在者或在場開顯者的信息。用「主─謂」式的表達方式來講,存在者或開顯者是主格或主詞,而一切有關前者的信息都是謂格或謂詞。在西方的傳統形上學裡,主格或謂格,主詞或謂詞,也就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哲學家所熟捻的「實體」與「屬性」了。
對一生命體而言,它所獲得或把握到的有關存在者或開顯者的信息乃是後者相對於此生命體而言的「意義」。「意義」是不單屬於語言,而是普遍地屬於一切存在者或開顯者的。你此時此地給我的信息,就是你此時此地對我的意義。但信息和意義是不能離開活動作用而言的,它們乃是運作於生命活動的權能產物──功能作用的產物。一切信息都是開顯於活動作用的信息。存在者或開顯者對一生命體的意義所反映的正是前者對後者所產生或可能產生的作用。老虎可以把我們吃掉,老虎這個可怕的作用不就是老虎對我們所開顯的信息和意義麼?故所謂一物的屬性也就是關於此物信息或意義的總和,亦即是它底功能作用的總和。如是,對存在或開顯的把握也就是對存在者或開顯者底信息和意義的把握──亦即是,功能屬性的把握。
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語言裡,這個立義於功能作用的屬性觀念一般都是用「德」、「性」、或「德性」這幾個詞語來稱謂的。一物〔開顯者〕之「德」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而「性」的原義是生,指的乃是內在於物的動態本質。故「德性」這個複合詞最能表達功能屬性的概念。回到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既然我們把生命體對存在或開顯的把握歸結為對存在者或開顯者底功能屬性的把握,那麼生命體是如何把握在場開顯者底功能屬性的呢?這個問題在根本上並不繁雜,是可以有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的。如上所述,開顯者的開顯乃是一依場而生的創化事件,一個由眾多的權能體和活動作用所蘊集而成的現實緣會;它的動態本質來自參與事件的權能體或生命體的互動或相互作用。在此互動或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開顯的不僅是某一在場者的功能屬性,而是所有參與者的功能屬性。我與他人他物在一事件中的互動不僅通過我自已而開顯了他人他物,也通過了他人他物而開顯了我自已。換句話說,開顯的不僅是我的自體牲,也是我與他人他物的互體性。總而言之,開顯乃是權能體的「共業」: 在互動中開顯的功能屬性乃是乃是權能體共享的存在德性。套用一個數學物理學的名詞,我們不妨說,功能屬性乃是一個多元多維度的信息矢量。
根據上文的闡述,為西方傳統哲學傳統所依賴的「主-謂格」語法和「實体-屬性」的概念範疇是不能確切地把握在場開顯者的開顯這個存在體驗的。具體物或權能體的功能屬性都是相對相關的;它們不僅相互外在與相互獨立,也同時相互內在與相互依存。此權能體的相對相關性或超切性正是「場」一概念在場有哲學中的勝義。說的準確一點,我們所謂的「場」,勝義的「場」,乃是萬物的胎藏,動態地貯藏著宇宙中一切生發與開顯的可能性與條件性。但這個「場」或「胎藏」本身並不是一具體物,也不是一個固定的處所或地方。構成萬物生發與開顯的可能性和條件性正在權能體的超切連續的共同屬性裡。以水與火為例,水能滅火或火能被水所滅這個功能屬性既不單屬於水也不單屬於火,而是水與火的擁有的共同屬性;這個共同屬性的信息矢量所指向的乃是潛存在水與火的內在關聯中的功能種子,一個場或胎藏中的可能性。水的定義中有火,火的定義中有水;由於水與火這個共同屬性,它們在存在德性上是相互定義的。對場有哲學來講,一切權能體或具體物的關係都可化約為共同屬性的關係:完全孤立的、離場或與場絕緣的自體性或自性是不存在的,無法開顯的。當我們用「主-謂」的語法來表達權能體或具體物的存在德性時,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忽略了或甚至切斷了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我們在描述或定義一物時往往剔除了他物的定義,切斷了開顯在一物中他物的意義或信息。
當我通過視覺的活動作用看到眼前的一顆樹的時候,開顯在我視覺活動中的不僅包括那顆直接地、頗為明晰地和界限分明地呈視在我意識中的形相的樹,還包括在我的視覺活動過程中間接地、隱約地和無形無聲地伴同著那顆形相的樹呈視它自已的創化權能。真正的存在者或開顯者不是那顆突出地呈現的形相的樹而是使整個開顯事件成為可能的生發主體──一個創化權能的分殊。直接呈現的、形相的樹只是創化權能於此時此地通過其動態本質所開顯的現象或殊相。但現象與本質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現象正是本質的開顯。前者乃是創化權能一體分殊的化身。因此我們不妨說,現象是創化權能在世存在的代表。作為宇宙永恆遍在的開顯者,創化權能正是通過它所開顯的現象、殊相或化身而成為此時此地的在場者。
創化權能通過活動作用而成為在場的開顯者,這是我們對存在最原始的體驗。 換言之,一切信息,最後分析起來,都是作用的信息,亦即是權能運作的信息。存在者或開顯者的意義乃是其作用的總和。如是,「存在乃是權能通過活動作用的開顯」這句話的內容主要可分開兩個主要方面來講,一是作用的傳承與互動,另一就是信息的感通與裁化。作用的傳承與互動是能,信息的感通與裁化也是能。此處「能」字兼有功能與能量的含義。我們稱作用的傳承與互動的功能或能量為「力能」或「力量」,稱信息的感通與裁化為「心能」或「心量」。作為創化權能一體的分殊,一切實有或具體存在都是由心力二能的交匯所構成的生命體。心力二能乃是生命權能之「雙翼」。生命不可「有心無力」,也不可「有力無心」。事實上,存在的開顯本身乃是一個「由力生心、由心入力」的創化過程。玆以下式概括之。
存在或存有在希臘及其他的印歐語言裡是以連綴動詞 (copula)「是」(on, ousia / being, existence) 來表達的,所以西方的存在論或存有論應該說是一種「是論」。有些學者更因此認為,由於漢文沒有與「是」相對應的語法,中國哲學是不能產生存在論的。
存在就是開顯者的開顯,這也許是我們對存在或存有這個概念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描述;存在者就是開顯者,開顯乃是一切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本質。一切有關存在或存在者的思想或言說,包括西方哲學的「是論」、中國的「道論」、和印度吠壇多的「梵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型態的「開顯論」,作者所倡導的場有哲學也不例外。本文的目的乃是通過場有開顯論的觀點來剖釋或探討一組相互關涉的哲學問題。場有哲學的一大特色在於它底非實體主義〔或簡稱非實體〕的立場。實體與非實體之爭衡過去已有過不少討論,但也引起了不少誤解。但隨著場有哲學一些概念和表達方式或語言的轉變,這個論題有重新處理的必要。實體的概念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在人類在人文化──文明化的過程中對開顯者的開顯所表現的姿態上。